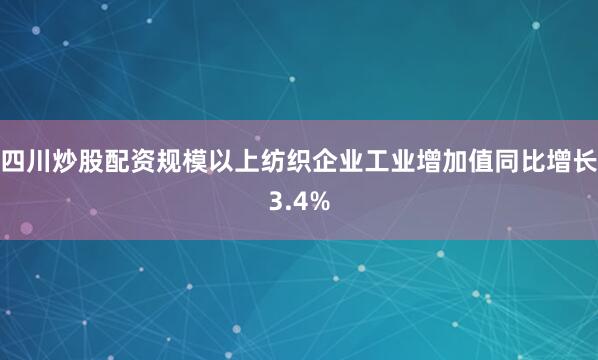#律师来帮忙#
作为我国城市管理的专门机构,城管上承政府,需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下接社会,直面民众多元需求。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场域。其不仅在宏观层面受体制环境与社会系统影响,微观层面被个体行动策略左右,更从宏观至微观整体性地受社会认同塑造。城管执法效果高度倚赖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是独立于个体、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作为外在力量深刻影响着城管执法的制度实践。然而,城管执法社会认同的生成存在疑问。广义而言,探讨城管执法社会认同论题,就是探讨社会心理机制对制度运行的影响,这是一个需在理论与实践的长期互动中不断反思、检验的问题。
城市执法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实践中多以“城管执法”形式呈现。然而,因城管执法内容和对象广泛,且基层社会情况复杂,城管执法常因日常利益冲突演变为公共冲突事件。一系列涉及暴力执法的舆论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城管执法的广泛质疑,其社会认同度也逐年降低。而城管执法社会认同下降甚至缺失,会严重影响城管执法效能与城市治理水平。破解城管执法的认同困境,并从制度层面进行优化,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所必须要直面的。城管执法社会认同的核心无疑是广大民众,他们基于自身经历、所见所闻,对城管执法的认知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持续不断地被建构、整合并长久延续。
城管执法冲突可视为执法双方争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特性影响行动者行为与认同模式,并生产出城管执法社会认同。城管执法多在开放、流动性大的街头空间进行,使用者广泛,违法行为随时可能发生,违法者情况各异,多“不情愿”成执法对象。城管执法多为直接致利益受损的行政处罚,矛盾对立多,带来不可知风险,且其权能单一、执法强制性不足,对街头空间秩序掌控有限。与之对照,行政审批机关在封闭空间工作,行政行为服务性强、关系稳定、风险小。其他部门职能单一却行为方式多样,城管职能综合却仅行政处罚单一职权。在社会转型期,城管执法空间模糊,易引发质疑、抗拒,冲突易放大,难以生产社会认同。
很多时候,公众对城管执法的不认同,反映的是超出执法行为本身的社会制约因素。当城管执法行动者自身面临生存难题时,这种社会性约束必然会在执法中显现,难以形成执法认同。城管执法虽具标准化,但执法者作为社会个体,呈现多样化特征。有学者指出,街头官僚存在激励不足、规则依赖等独特行为逻辑,并非按理想“公正执法”模式行动。比如,按法规无照经营不被允许,但因无照经营数量多、变化快且被视为既定事实,执法人员执法时可能留有余地,检查过严会遭抵制、带来风险,上级检查也不严,形成默契,致使理想“公正执法”与现实背离。可见,城管执法社会认同在复杂社会现实制约下运行。
现代传媒对城管执法社会认同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能正向放大认同,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门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展示良好执法形象,吸引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像南京鼓楼城管通过微信公众号、智慧审批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简化市民办事流程,让市民成为城市“管家”,借助新媒体传播拉近了与市民的距离,增强了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更多情形下它可能放大不认同,无处不在的网络将城管执法置于公共舆论中心,接受审视、质疑与拷问。在当代大众媒介中,“城管”一词缺乏严肃性与权威性,甚至成了被戏谑嘲讽的符号,如城管污名化,且现代信息技术让媒介有了“社会权力”,摆脱了对权力的“谄媚”。
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肩负维持秩序之责,与管理对象存在利害关系,易生矛盾,部分低素质城管野蛮执法,加之小商贩等执法对象文化程度不高,矛盾极易尖锐化,甚至出现双方暴力相向的情况。有人提议取缔城管,将其工作分给警察等群体,虽有一定道理,但城管存在已久,取缔不易,维持现状更不可行。当下城管亟需整队,净化队伍,清除不合格人员。城管代表城市与政府形象,必须提高素质,开展二次培训,严惩粗暴、越权执法者。同时,建立合理监督考核机制,适当将百姓满意度纳入评价,罚款与绩效脱钩。此外,城管执法时要有同理心,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小摊贩等着想,与之建立良好关系,以获民众认同。
股票安全配资,沈阳配资开户,网上炒股加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平台导航她们会在30年后对簿公堂
- 下一篇:找股票配资不能让日本出现政治真空